
记忆中的父亲


独家抢先看
父亲名绍贤,字云端,生于1904年(光绪30年)甲辰正月17日丑时,1975年乙卯7月27日亥时因脑溢血去世,享年71岁。
我自16岁离家去宁海县城读书,继而工作,又去读书,1974年分配到宁海县文化馆工作,直至1975年夏天父亲去世。期间虽然经常回家看望父母,但总是聚少离多,所以对父亲的人生历程知之不祥。作为儿子的我亦已步入晚年,早就想写点父亲的事迹而一直未能如愿。值此父亲辞世45周年之际,试图写出记忆中的“父亲片断履历”以为永久纪念。

图1,父亲69岁像,1973年摄
一
1923年初春,时年19岁的父亲为了谋生,经一位定居在上海的族叔(我叫开正公)介绍,去上海私立复旦大学当门卫,门卫的工作任务是为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整理并发送邮件书信。父亲虽然仅上过几年私塾,文化不高,可他的外貌却清秀可人,很像一个白面书生,以至于有些女大学生误以为他是“复旦男生”,对他颇有好感。当得知他是一个“门卫”之后,便一反往常地冷淡了。这种感觉,对于一个19岁的青年是很不好受的。为此,父亲在复旦大学做了一年不到的门卫工作就离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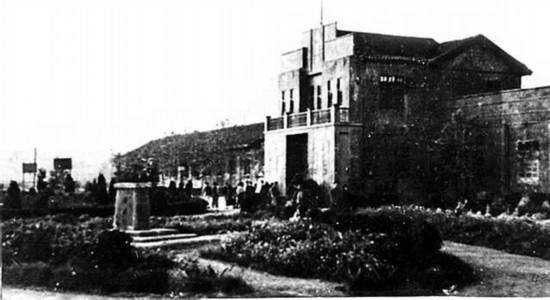
图2,1923年的《复旦大学》
二
1924年,又是这位好心的开正公,第二次把父亲推荐到上海有名的大寺院——龙华寺。龙华寺位于上海市南郊龙华街道,是上海地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古刹。龙华寺的名称来源于佛经中弥勒菩萨在龙华树下成佛的典故。据传,龙华寺乃三国时期吴王孙权为其母所建,距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
龙华寺的方丈法号元谯,世称“元谯和尚”,其祖籍是宁海县黄坛镇灵山村(俗称瓦窑头),原名麻德根,生年不祥,青年时即出家,入佛门上海龙华寺 ,圆寂于民国29年(1940年)。这位方丈很看好我的父亲,认为他外貌标致,为人朴实,办事顶真,又略懂算数和书法,当然还有“同乡三分亲”的缘故。于是没多久就升任父亲为龙华寺方丈助理。所谓助理,就是保管、整理寺院的随缘乐助财物和名人书画等。为了报答元谯和尚的知遇之恩,父亲勤勤恳恳地打理寺院的进出物事,还经常陪同一些信佛的上海阔太太去安徽九华山进香拜佛,期间,他认识了张嬷嬷、李嬷嬷、赵嬷嬷、金嬷嬷等上海名流的家眷。
父亲在龙华寺还结识了一位法名叫“铁锤”的和尚,铁锤和尚不仅是个武僧,而且还写得一手好书法。其行书学隋代僧人智永的《千字文》,其草书学唐代僧人怀素的《自叙帖》。因为父亲钟爱书法,所以经常为铁锤和尚磨墨理纸,倾心学艺,诚意请教,受益匪浅。上海商会会长王震即是大名鼎鼎的大画家白龙山人王一亭。王一亭一生奉佛,是龙华寺的常客,还与铁锤和尚交谊甚厚,因此父亲时而得见白龙山人高谈阔论,时而目睹白龙山人泼墨挥毫,其气度与技艺不愧为大家风范,他的留于寺中的墨宝数量不少。父亲曾多次跟我说:“在龙华寺的三年真是大开眼界:善男信女、云游高僧、文人墨客、商贾大佬、达官显贵等三教九流人物各呈风釆,天天见识,日日目染,胜读三年书啊!” 就这样,父亲在龙华寺风风光光地做了三年方丈助理。1927年初,父亲23岁,我的爷爷催促他回家拜堂(结婚)。父命不可违,婚事不可拒,他只好忍痛割爱地告别上海龙华寺。父亲在龙华寺的三年,应该说是他人生经历最为精彩的片断。他经手过大量“随缘乐助”的钱财,保管过无数金银珠宝和名人书画,可他离别寺院时却净身迈出佛门,清爽回到家乡,此等身心,真可谓一尘不染啊!

图3,1925年的上海龙华寺

图4,1925年的上海龙华寺

图5,王一亭与吴昌硕
三
父亲在上海龙华寺的3年中,颇受铁锤和尚的影响。从龙华寺回到老家后,他在参加农业劳动之余,经常练练书法,而且写得不错。他始学欧阳询的《九成宫》楷书,继而学“二王”及智永的行书。家里正房南窗下的一张八仙桌上,固定放着一本记工分的日记本,本子是用浅黄色的元书纸线装而成,本内写滿了一行行的毛笔行楷,字体劲秀而略带拙味。我读初小时,父亲时常督促我练习书法,还手把手地教我“描红”或临摹。直到我青年时,还经常对我说:“不管楷书和行书,结构都要紧凑团缩,但每个字总归有一笔要拉开,这样,写出来的字就会既端庄又灵活。”我自20几岁开始就初生牛犊不怕虎地为人家写春联了。每当我在家里这张八仙桌上书写时,父亲就会不厌其烦地帮我拉纸头,书写后的春联挂在房内的板壁上总要探讨评论一番,在农村的家庭中有这样的文化氛围,也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
村族中的多数家庭都有传统的“堂号”和“记号”,我家是“陈积善堂”、“和记”。家里的主要农具都留有父亲书写的“陈积善堂”及“和记”的楷书字样。1980年,我调到宁波后,还从宁海老家带来一对“竹蔑米箩”,米箩的竹骨架上就有父亲书写的“陈积善堂和记”,这是父亲留在家中唯一的书迹,可惜这对米箩在2004年搬家时发现霉烂散架了。二年后,我有幸在老家民间觅得一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竹套篮(旧时盛果品或盛饭菜用),套篮的竹篾架上书写着几个欧体楷书,据说是父亲书写的。经仔细辨识,基本上可以确认是父亲的手迹,窃以为绝而复现,欣喜异常。这只套篮上的欧体楷书是父亲在1931年27岁时所写,已经显见功力了。
我家的这个堂号和记号,估计已经延袭好几代了。翻开《竹溪陈氏光兴公系下房谱》,即可查阅到父亲的曾祖父“万辂,字允乘,号绍商。太学生,官名守年……”这样的文字资料。而太学生万辂公的祖父天炯先生则是一位私塾老师,能文章,工诗赋。天炯先生培育的一位侄子中了举人,二位孙子均为太学生。天炯先生之父尔琳,自幼读诗书、学文章,稍长又耽情于孙吴韬略。青年时弃举学医,于宁海城内挂牌门珍,宗精外科,名闻四方,有活华陀之称。从这些简约的房谱资料可以看出,这个富有儒家意味的堂号和记号是历经几代传承下来的,而父亲浓厚的传统文化意识的形成亦有遗传因素。


图6,父亲留世的唯一书法


图7,父亲留世的唯一书法
四
记得在读小学前,每逢冬季的晚上,我都和父亲并头而眠,每当早晨醒来时,父亲往往会教我唱一些著名的历史歌曲和抗战红歌,如:《苏武牧羊》、《孟姜女哭长城》、《送别》、《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义勇军进行曲》和《东方红》等。尤其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和《东方红》这二首,更是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教唱,直到唱背为止。同时,还穿插讲些打日本鬼子的故事。不管父亲出于何种意图,至少在客观上起到了对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1949年解放后,父亲满怀激情地在靠餐桌的板壁上贴了一张毛主席像,像的左右二边分别写了“共产党万岁”和“解放军万岁”的红纸条幅,毛主席像上方的横额则写了“毛主席万岁”。在快要解放的前夕,父亲还把在上海做“娘姨”的二女儿叫回老家,解放初还叫她参加了革命队伍。父亲的这一系列表现,其爱党爱国之情怀,显而易见。
图8,《突破鬼子封锁线》陈承豹作 2012年

图9,《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五
1953年至1956年期间,父亲曾分别在宁海县土产公司(后改名副食品公司)和竹口乡供销社做炊事员。宁海县土产公司位于宁海城关中大街西段与小北门路相交往北拐弯的不远处,大门朝西,是解放前一位大户人家的四合院,四合院中央是一个偌大的石板道地。一年四季,每逢阳光灿烂的天气,道地中就会晒满散发着各种香味的土特产,诸如大黄鱼鲞、乌贼鲞、大对虾干、黑枣、红枣、白木耳、黑木耳等等。儿时的印象中,那时的物产太丰富了,而且毫无污染,质高量多。有一次,公司里的二位青年职工,脸上涂满了黄糖在相互追打戏耍。这种好玩的情节,是否可以说明当时的物产丰富得竟可当作玩具?
1953年,我时年8岁,父亲第一次领我到宁海县土产公司玩,并小住了几天。一天早晨,父亲起床去厨房工作,我还在床上躺着时,突然听见隔壁(板壁)一个青年职工轻轻地戏叫了几声“烧饭佬的儿子”。当时的我虽说年幼,但这话却深深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我隨即起床,跑到父亲跟前告了状。父亲听了这话后并没有生气,但面部表情略显凝重地对我说:“你父亲因为文化不高,所以只好当当烧饭佬。你以后一定要好好读书,要学点本事,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父亲这几句虽然简短的话,对我却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从读小学开始,父亲对我的教育开始有所严格。他在竹口乡供销社烧饭期间,因为该社距离我家较近,所以我就会隔三岔五地去那里玩。供销社的六七个职工大都回家过夜,而父亲则往往在单位值夜班。一天晚上,我看到琳琅满目的山珍海味、糖果饼干等整齐地摆放在店内,就好奇地问父亲:“介多好吃的东西放在这里,又没有工作同志看管,可以拿几样吃吃吗?”父亲把脸一沉,严肃地问我:“你想当贼骨头吗?”我说:“不想!”“这就好,你记住,凡是人家的东西和公家的东西都不能拿,拿了就是贼骨头,做了一次贼骨头,就会被大家一直看不起,以后做人就难了!”父亲还是一脸严肃地说。读三年级的我已经很有明理的意识,听了父亲这一席掷地有声的话语,差一点赫出冷汗。从此以后,“一个人决不能做贼骨头”的警示深深地刻入我的脑际。

图10,少年当自强
父亲为人低调老实,品格端方,办事严谨,勤劳艰苦,刚正不阿。对下一代的教育理念是严格与慈爱相结会,志存高远与顺其自然相结合。育了二女一男,各有成就,还算争气。后代分杈,枝繁叶茂,人丁兴旺。在天有灵,保佑香火不灭,保佑代代相传。
2020年7月27日
敬撰于砚香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