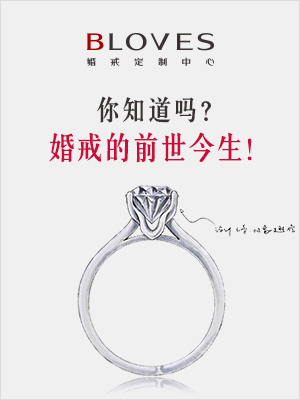浙江宁波:融合自治“他们”能否 变“我们”
2011年12月07日 10:24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杨洋
摘要:新一轮民工荒下,长三角与珠三角在抢夺劳动力资源的竞争中略占上风。这里一样有着霄壤之别的贫富鸿沟,农民工一样有着根植内心的弱势感,但不同于珠三角的是,这里的超级民营企业,没有南方富士康王国式的管理
摘要:新一轮民工荒下,长三角与珠三角在抢夺劳动力资源的竞争中略占上风。这里一样有着霄壤之别的贫富鸿沟,农民工一样有着根植内心的弱势感,但不同于珠三角的是,这里的超级民营企业,没有南方富士康王国式的管理。农民工下班后各回各家,不是集体中的一颗螺丝钉,而是组织松散的社会人,并与当地人建立了融合自治组织,这就是所谓的农民工服务管理“宁波模式”。

王芳萍把15年的青春留在了宁波余姚小路下村(杨洋摄)

王芳萍在这小屋住了10多年,对这些年本地人和外地人关系的变化有切身体会(杨洋摄)

25岁的胡景芳从力邦社区物业部门的办公室里走出,她是这里的一名工作人员。浙江宁波奉化西坞街道力邦社区是全国首个外来务工人员自治组织。新华社资料图

样本意义
新一轮民工荒下,长三角与珠三角在抢夺劳动力资源的竞争中略占上风。这里一样有着霄壤之别的贫富鸿沟,农民工一样有着根植内心的弱势感,但不同于珠三角的是,这里的超级民营企业,没有南方富士康王国式的管理。农民工下班后各回各家,不是集体中的一颗螺丝钉,而是组织松散的社会人,并与当地人建立了融合自治组织,这就是所谓的农民工服务管理“宁波模式”。
浙江余姚小路下村从经济组织上看,就是典型的“一个村庄一集团”,村委书记就是云环集团董事长。这个2.56平方公里的小村庄,户籍人口3400人,年工业产值39亿元,6000多外来工是一线生产的主力。经过二十来年的共生共荣,他们鲜有风起云涌的对抗,却在暗自角力中不断寻找着平衡点。
一个动作每天重复六七千次
第一个月拿到680块钱工资时,王芳萍觉得再苦都值了,这可是家乡村干部两个月的工资:“我当时真是用颤抖的手签下领款名字的。”
层高近5米的车间里,阳光从四周的宽大窗户里打进来,经过通风机的搅拌,或明或暗地闪烁着。昼夜开启的白光灯,把上千平米的车间光线调得均匀明亮。44岁的安徽肥西下江人王芳萍,和数十名工友常年工作于此,对这种人造光更觉得适应。
灯光下的电线或黑或白,按照不同品类,数十根一捆,面条似的挂在架子上。偶尔在翻腾的线卷中冒出一两个人,低头检验质量。放眼望去,数以十万计的电线,能让密集恐惧症患者生畏。厂房内一般比室外高出一两度,时值八月,这片半成品在30多度高温下,隐隐散发出胶着的塑料味。
在这样的空气里,王芳萍穿着画有硕大G U C C I字母的T恤,毫无顾忌地咧嘴笑着,一边和工友唠着家常,一边用右手执起电线,用食指的硬茧抵住线头一寸的地方,将其送进打口机,左手咔嚓一声按下,就给一根电线接上了头,一分钱的计件工资进了口袋。
厂里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完成这样的动作要四五秒,王芳萍三秒内就能搞定。这样的动作她每天重复少则六七千次,多则上万次,食指指头关节处已成三角形,上半部分发达变大,下半部分因为常年摩擦凹了进去,一摸全是硬的,她戏称这样干起活来全无痛觉。
15年前刚到小路下时,王芳萍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电线厂,做的是从机器里拉电线的活,第一个晚上就拉得肩膀都抬不起来,半夜里对着墙壁无声啜泣。然而第一个月拿到680块钱工资时,她觉得再苦都值了,这可是家乡村干部两个月的工资:“我当时真是用颤抖的手签下领款名字的。”
十多年过去,当年泥泞小路上的三五间工厂,现在已发展成连片的高大厂房,几乎每家都冠上“云环集团”几个大字。在这个不大的村庄,除去家庭小作坊,40多家氟材、模具、开关、电脑配件、电缆电线等民营企业,全属云环集团名下,有种“莫非王土”的霸气。
一身工服从赶鸭子到放鸭子
“以前也搞过集体宿舍,后来大家都愿意100来块租房住得自在,吃饭也回家,下了班就没人管。”王芳萍说的,也是许多北下农民工看中的一点。
不过与南方的大型工厂相比,云环集团似乎少了些无孔不入的“威严”。即使在云环高科技的登天氟材厂,对技术要求最精细的裁衣组师傅叶小兵,也没有穿统一的工服,而在电线厂的王芳萍穿着就更随意。虽然从劳动保护的角度看,身着便装意味着剪线时金属尘屑可能会打在毫无防护的脸上,而橡胶味道也会影响嗅觉,但从王芳萍和工友们看来,这意味着可以摆脱某种职业定式。
“我去年才从广东过来。”36岁的莫许钊是四川人,个子矮小,皮肤黧黑,思考时一使劲就把眼睛挤成一线,“广东的大厂车间看得很紧,(流水线)上面的工做完了,轮到你还不动手就被说。
莫许钊说,熟练工都指望大厂效益好,可南方大厂里甚至连吃饭时间都分好,吃不完也得轮到下一批,“跟赶鸭子似的”。而在这里的大厂,他能感受到“放鸭子”的氛围。
王芳萍所在的登天电缆虽属云环集团,但整个集团是从村镇企业发展而来,1999年改制成为民营企业,2000年后出现井喷式布点,管理上大而化小,各工厂更接近独立的中小企业。“以前也搞过集体宿舍,后来大家都愿意100来块租房住得自在,吃饭也回家,下了班就没人管。”王芳萍说的,也是许多北下农民工看中的一点。
从整个余姚县来看,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民工荒的大环境里,这里的外来工人数仍有连年微小的增长,今年前八月同比增长1.13%。
现在还留在工厂里说着吴侬软语的本地人,除了老板,大多就是业务骨干或者高级管理层。上班时,余姚另一家机电厂的本地模具数控师傅戴桢磊,穿着和普通工人一样的深色衣服,辗转各个车间,和外来工老蔡谈论着冲模的情况,也闲话一下家常。
“嘀铃铃”下班钟响以后,本地人和外地人才看出差别来。王芳萍的两位同乡大姐还一屁股坐在插头堆里,争分夺秒地多攒几个任务;一个男人没等人走完,就一把将作业台上的插头推开,理出一片空地,倒头在上面呼呼地打起了盹儿。
手脚麻利的王芳萍按时收工,走回小河那头的出租屋,惦念着昨日留下的小炒肉,加上两块钱咸菜,就是一顿简单的饭。经过小路下村委门前的那条路,简单搭置的大排档,把桌子都摆到了马路上。炒三两个十几块钱的肉,加一瓶冰啤酒,工人们吃得欢畅。厂里驶出的宝马、奔驰、雷克萨斯,从人和桌子的间隙鱼贯而出。戴桢磊这时也开着私家车回家,对于老蔡们聚居的“村中村”那片低矮的平房,十多年来他只踏足过三两次。
一次误会发现猜疑如影随形
“她说我偷了厂里一把割电线的钢刀。”王芳萍很委屈,“我要那个刀做什么呀!”本地人很快围上来,后来两人回工厂对质,才在线堆里找到了钢刀。
在这个外来工人数是本地人两倍的村庄里,两者以8小时为界限,维持着朝夕相处又保持距离的关系。
形成今天这种关系,他们用了十多年的时间。1996年初,29岁的王芳萍,揣着200块钱,从家乡肥西坐车到小路下的时候,本地人群体是他们很难进入的圈子。
与珠三角原住民收地租的传统不一样的是,十多年前的江浙本地人就以进厂打工为荣。根据余姚市志,1995年,整个余姚市外来务工人员只有2.8万。在此之前,整个宁波实行严格的“先本地后外地”就业政策,市劳动局专设外来劳动力管理处,招聘外省工人需要通过其审核并批发指标。四川泸州人韦应龙,就是1994年当兵退伍后,到小路下模具厂打工的。他当时不知道的是,自己这种不经登记的外来工都是打工黑户,每次“上头”有人来检查,都要将黑户支到大路上游荡。
当时在劳动力管理处工作的陈发泉回忆:“那时招个外来工就像用个外国人那么难。普工岗位本地人优先,实在本地人做不了,打报告才能请外地人。”小路下村原本的岗位都由本村人消化掉,然而1996年随着工业扩张,就业政策开放,面对慢慢多起来的外地务工人员,原本自成一体的本地生态也发生了排斥反应。
王芳萍至今记得那个赶工加班后的夜晚,她走回河边出租屋,一路上一直有个同组的当地女工随行。等她拿出钥匙正要开门的时候,那个女工突然大喊抓贼。
“她说我偷了厂里一把割电线的钢刀。”王芳萍很委屈,“我要那个刀做什么呀!”本地人很快围上来,后来两人回工厂对质,才在线堆里找到了钢刀。
王芳萍这才想起,之前跟本地人借个柴米油盐,对方总是让自己在门外等着;有时走进本地人的屋子,总有个身影跟在后头,原来他们都在提防着,“怕外地人偷东西”。自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性格开朗的王芳萍,采用了中国农民对待矛盾最惯常的方式:沉默。她在厂里跟头牛似的埋头苦干,拉电线拉到脖子疼也不哼一声,更不跟工友说一句话。
一声“他们”隔阂埋下的导火索
一些“滑头的人”没找到工作,常在村口聚赌,王芳萍的一个安徽老乡就在其列。“他见过我把钱糊在墙壁的报纸里,一次来我家唠嗑,后来我转身出去再回来,藏在里面的钱就没了。”
虽然王芳萍受了委屈,但生性耿直的她也不为老乡护短。小路下村综治办主任钱兴成是本地人,做治安工作这么多年他最清楚,大部分的治安案件的确跟外地人有关系。
特别是1999年,小路下实行村镇企业改革以来,村里从刚开始的8家乡镇企业和一些小作坊,要在10年里扩张到40多家企业,也就是后来的云环集团,外来人口成倍地涌入。
林子大了,就有一些“滑头的人”,没找到工作,常在村口聚赌,王芳萍的一个安徽老乡就在其列。“他见过我把钱糊在墙壁的报纸里,一次来我家唠嗑,我还奇怪他用脚划了划墙壁,后来我转身出去再回来,藏在里面的钱就没了。”王芳萍顾及老乡关系没有报案,但这个人的品性慢慢传开,十年后的今天,还可以见到他胡子拉碴,和小辈的九零后一起游手好闲。
正因为这些,外来人成为本地人口里的“他们”。2000年前后,“他们”大量涌入,参与到新机器扩大的生产中去。当时找工作,十几个人排队到厂,一般都成批地全被收进厂里,经过一两天的加强培训,就能上岗操作模具,而现在的技工学校少则也要学习一年多。
在一次操作时,韦应龙抱着侥幸心理,把一颗拇指大小的物料放到擀面机一样的机器中,来不及抽手,就咔嚓一声听到自己骨头碎裂的声音,血浆染红了操作台,他的右手四指被轧断。至今,余姚本地还流传这样的说法:“‘他们’有人专门靠断指碰瓷,一个赔两三万,拿了钱换另一家,所以许多厂都不敢接断指工。”
韦应龙完全不能接受这种揣测:谁会把这钻心的疼拿来换钱。好在他是老员工了,老板最后赔了医药费,可再也没有模具生产线肯接纳他。
“他们”与本地互不信任的隔阂一度变得紧张。钱兴成调解过一个案子,两个11岁的小孩一起玩耍,籍贯四川的孩子毛伟有过失,致本地孩子刘源摔倒以致入院。刘家家长向毛家索赔药费,村委会裁定毛父赔18000元,毛家不服,认为“村委会总是偏帮本地人”,还带了十几个四川老乡搬着凳子坐到刘家门口,一时间四川人和本地人剑拔弩张。
“外地人和本地人的一小点矛盾,都可能成为导火索。”钱兴成两边说,两边都听不进,最后他出动了几个四川老乡,给毛家讲理,没想到,他们一下子就被说通了。钱兴成想,不见得老乡说的话一定比综治办多些什么魔力,而是老乡的这层身份,就有很强的说明力。
一次风波老乡出面震住全场
王芳萍起初认为,和谐联谊会不过是中秋节时一起搞个晚会,平时一起开会谈谈计生的一个组织,但后来发生的事件改变了她的想法。
综治办从经验中慢慢获得一些要领。2007年,邻市慈溪的坎墩街道,作为外来人口出租屋集中地,首先推行了一种本地人与外地人对半成立的和谐促进会,共同处理外地和本地矛盾。
钱兴成闻悉,召集了王芳萍、韦应龙等人,作为小路下村来自安徽、四川、贵州等地的外来工代表,商量成立这样一个融合型组织:外地人和本地人各占一半,学坎墩进行“外人治外”。可坎墩街道主要是外地人聚居生活的地方,而小路下整个村就是一个大集团,连生产工作的事也要纳入管理,能行么?
2007年7月13日,钱兴成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老钱当会长,村委会主任和一位四川老支书龚富强做副会长,加上25个首届和谐联谊会的理事,挤到文化广场的台上,鼓掌剪彩完成了仪式。
首届和谐联谊会有25个人,其中本地人12个,外地人13个。王芳萍起初认为,这不过是中秋节时一起搞个晚会,平时一起开会谈谈计生的一个组织,但后来发生的事件改变了她的想法。
就在联谊会成立后不久,村里突然爆发了一次200多人的群体性事件。起因是一个安徽工人和一个四川工人在车间工作时,因为抢一件物料争执起来,短短一小时,各自纠集了100多个老乡,拿着各式工具,气势汹汹地将村口的路都堵死了。进进出出的车辆被堵在外围,也不敢随便按喇叭,谁都担心火药桶一触即发。
钱兴成赶到现场时,人群开始向治安队的车靠近,治安队转眼成为焦点,钱兴成想起当时那个场景至今还有点后怕。但就在这时,副会长龚富强夺过钱兴成手中的话筒,站上高处,用四川口音朝人群吼道:“有什么事情,我们办公室里说。相信我,好不?”
龚富强1960年生,皮肤黧黑,原来是四川泸州下边一个村支书,之前当过兵,曾经是个团级干部,虽然迫于生活出来打工多年,但是在人群里那么一吼,气场还是把许多人震慑住了。
结果,四川人首先放下工具,为首的几个乖乖跟着老龚去了办公室。安徽人这边一个巴掌拍不响,也四散离去。钱兴成这些年来没少见过群体事件,但那次他真心佩服龚富强,“没有他的话,不会这么顺当。”
一河之隔本外界限仍难逾越
“在河这边看着对岸嫁女儿,十几辆车那么长的车队,红地毯也铺了几里,排场一个比一个大。”王芳萍也说不上眼红,反倒慨叹,最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的4年,小路下村再没发生过这么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联谊会每月定期开一次会,讨论内容因时而定。像今年年前一次会议的主题就是鼓励会员回乡多带人来务工,平时会讨论外来工公寓楼的分配以及儿童疫苗接种等问题,8月份的讨论话题则是外来工子女上公校的需求。
贵州的胡永龙夫妇在小路下务工,大儿子读三年级,今年想把小儿子送到几村合用的公办湖北小学读书,通过联谊会给钱兴成递了个纸条。宁波近两年推行尽量安排民工子弟读公校的举措,按照余姚教育局统计,今年余姚3.8万小学生中有1.9万是外来工子弟,工业区学校的农民工子弟甚至达到2/3的比例。
“学位当然抢手,但我们本地人还是能走走关系,帮忙把孩子送进去。”钱兴成说,每年通过联谊会送来的条子很多,只能尽力去办。
根据宁波市外来人口管理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截至2010年8月,全市民政部共备案登记的社会融合组织已达2868个。虽然各地区的融合组织发展程度不一,但这种“外人治外”的自治模式,一定程度上消化、缓解了外地人和本地人交集地带的一些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当地妇联、计生和就业服务等日常工作上令下达。小路下村今年决定将外来工会员扩展到600-900人左右。
南方都市报“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专题报道特邀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崔传义,在国务院农民工办的一项课题研究中,专门探讨了这个“农民工服务管理的宁波模式”,崔传义认为,“在主动改善和推进以破除二元结构、融入城市为趋向的农民工服务管理工作,做出了示范性的尝试。”
王芳萍对这些宏观层面的解读一无所知,她还是住在河畔那个十平米的小房,不过发生变化的是,由于在村里有了资历,加上联谊会理事的身份,现在她走到哪里,不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主动跟她打招呼。
随着河这边工厂的扩张,小路下村的农民工大军也越来越壮大,河那边的别墅和私家车越来越豪华。“在河这边看着对岸嫁女儿,十几辆车那么长的车队,红地毯也铺了几里,排场一个比一个大。”十几年间打工者工资涨了十倍,而本地人财富的增长则远不止这个数。王芳萍也说不上眼红,反倒慨叹,最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现在我走在街上,本地人都跟我们打招呼,没觉得有什么区别。”王芳萍虽然这么说,但当她听说高中学历、20岁的女儿,谈了一个余姚本地大学毕业的男朋友时,心里还是很忐忑。她看过那个男孩子的照片,生得端正帅气,家里开的车也不差,她老对女儿说:“你说,这么好的一个本地人,没缺鼻子没缺啥,怎么会看上你呢!这是不是做梦呀!”
大事记
2003年
1月7日- 8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指出: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发挥城市对农村带动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2月中旬,广东省首先发生传 染性非典型肺炎流行。随后,广西、山西、北京等地也陆续发生非典疫情。这一持续数月的疫情对农民工流动造成极大影响。
3月17日,任职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 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三无”人员收容站。次日,被送往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在这里,孙志刚遭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 蛮 殴 打 ,于3月20日 死 去 。“孙志刚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
3月2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4月3日,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举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推开,这是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
6月18日,中国政府和泰国政府签署协议,双方将从今年10月1日起,实现蔬菜和水果产品贸易的零关税。
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381号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办法》共18条,包括对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的原则、救助站设立和管理、为求助人员提供的救助内容、救助站工作人员的行为,以及违反者责任追究等,标志着我国对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
7月11日,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关于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个人取得农业特产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决定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停止征收农业特产税,改为征收农业税后,对个体户或个人取得的农业特产所得,按照有关规定,不再征收个人所得税。
12月25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闭幕。会议系统总结了2003年农业和农村工作,全面部署了2004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着重研究了促进农民增收、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深化农村改革等问题。
整理:方军
总策划:曹轲庄慎之任天阳
总统筹:王钧南香红张蜀梅
学术支持: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
出版合作:花城出版社
摄影统筹:王景春潘劲松
网罗天下
频道推荐
智能推荐
图片新闻
视频
-

滕醉汉医院耍酒疯 对医生大打出手
播放数:1133929
-

西汉海昏侯墓出土大量竹简木牍 填史料空缺
播放数:4135875
-

电话诈骗44万 运营商被判赔偿
播放数:2845975
-

被击落战机残骸画面首度公布
播放数:535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