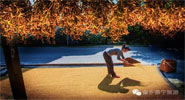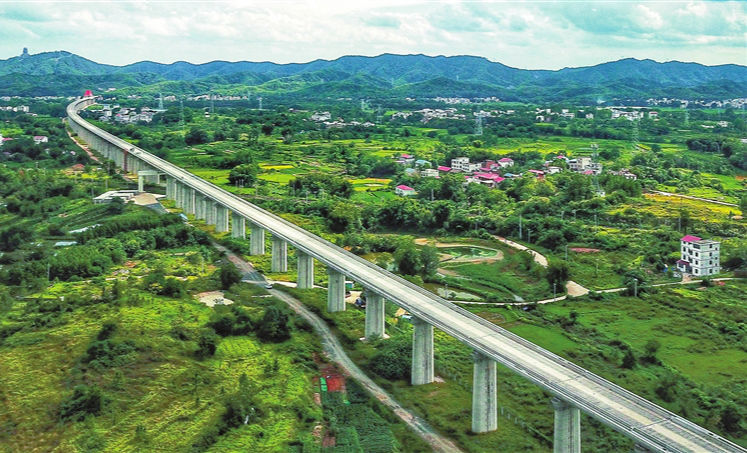诗歌里的宁波年味:香多吸老酒,鲜极破黄鱼
2017年01月15日 06:48
来源:浙江日报 作者:张如安
中国古代涉及饮食的诗歌比比皆是,在《诗经》中就可见到不少,此后饮食也成为作家的公共话题,“味”也以此成为中国文学的基本素材。雪菜和黄鱼堪称宁波菜的绝配,两者互烧竟能将黄鱼的鲜味发挥到极致,其所形成的味鲜的确是无与伦比的。
中国古代涉及饮食的诗歌比比皆是,在《诗经》中就可见到不少,此后饮食也成为作家的公共话题,“味”也以此成为中国文学的基本素材。
我国古代的饮食文学,以诗词最多,也最具美学价值,可惜古代并没有因此发展出具有独立品格的饮食文学创作类别,饮食大概只能充任文学史上的“佐料”角色。即便是以饮食为主题的作品,也是应景之作居多,除了苏轼、陆游等大家外,除了酒和茶两大题材外,鲜有人肯下大力气进行创作,故从总体上看,饮食诗歌难以产生上乘之作。像苏轼《惠崇春江晚景》这一类的涉食佳作,古人并不将其当作饮食诗来看待,但这并不妨碍后人选择饮食的视角进行解读。
美国学者安德森观察宋代饮食风尚时,就发现宋代文人对食物“做了了不起的科学观察”,这在饮食诗中能找到很多例证。自宋以来,举凡食品的生产销售、民间习俗、烹饪食疗、掌故轶闻、时令节俗、宴饮情趣等莫不有诗,社会的变迁也在饮食的一角留下了诸多历史痕迹。
从饮食诗中可以考见食品的制作技术,如元代鄞籍女诗人郑允端有《豆腐》诗写道:“种豆南山下,霜风老荚鲜。磨砻流玉乳,煎煮结清泉。色比土酥净,香逾面髓坚。味之有余美,玉食勿与传。”这里,“玉乳”二字形象地说明磨中流出来的是豆浆,表明用来做豆腐的大豆要浸泡后就磨,磨时还要加水。“煎煮”就是将磨出的豆浆加热煮沸的意思,这是豆腐制造中既重要又必须经历的一步。“结”为凝结之意,与上句的“流”相对,意谓乳浆经“煎煮”竟使“清泉”凝结,这是煎煮中不用凝固剂的自淀法,所成豆腐比萝卜色白,香气四溢。
从饮食诗可以考见食者味觉的变化。明代鄞县人吕时《沈世君问宁波风土应教》诗中有“香多吸老酒,鲜极破黄鱼”之句,“香”和“鲜”被放在句首,不仅突出了食者的美味感受,且在客观上张扬了中国烹饪的二元价值标准。特别是将黄鱼作为下酒之菜,挑破黄鱼送入口中的味道是“鲜极”,更让我辈别有会心。吕时向外人夸耀的,很可能是雪菜大汤黄鱼。雪菜和黄鱼堪称宁波菜的绝配,两者互烧竟能将黄鱼的鲜味发挥到极致,其所形成的味鲜的确是无与伦比的。
其实很多食料都有呈鲜物质,可以在汤水中释放,但在海鲜菜的味型上咂出“鲜极”,由此足见宁波食客味蕾的发达了。看来,明代人对于鲜味的独立认识,应该有着宁波海鲜菜的一份功劳。
不同国家和民族因为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的不同以及对风味爱好的差异,对味的分类也有所区别。中国人的基本味觉分为苦咸甜酸辣五味,日本人的五味中却有鲜味,但欧美地区不把鲜味作为独立的味,到目前为止,英语中还没有哪个词汇能准确描述出由日本人发现和定义的第五种味觉——鲜。从鲜味的历史看,明代吕时因海鲜菜而咂出“鲜极破黄鱼”的味蕾感觉,在烹饪史上就更有意义了。
从饮食诗中也可考见在某些地区已经失传的社会风俗。如采茶歌是古代广泛流行于我国南方的劳动民歌。四明山区的采茶时节,山中总能回荡着采茶女或悠扬或幽怨的采茶歌,这是她们情感生活的自然流露。如诸观光《采茶歌》云:“露华风叶掇新枝,采采春光好采之。谁道隔花莺语滑,阿侬随口唱歌儿。”张志蕙《采茶歌》云:“篝灯午夜彻山阿,火候当垆费揣摩。少妇不知春事换,焙茶犹唱采茶歌。”周铿华在《采茶曲》小序中写道:“越女采茶率连声合歌,而词多鄙俚,音非风骚。”可见古代越女在采茶时,常常唱起那娇若莺啭的艳曲,此起彼伏,煞是动听。可惜这些词多鄙俚的采茶曲没有流传下来,否则我们又多了一项非遗。现在流传下来的文人们拟作的采茶歌,内容丰富,情感浓郁,仍保留着一些原生态的生活汁液。![]()
[责任编辑:陈红珍]
- 好文

- 钦佩

- 喜欢

- 泪奔

- 可爱

- 思考